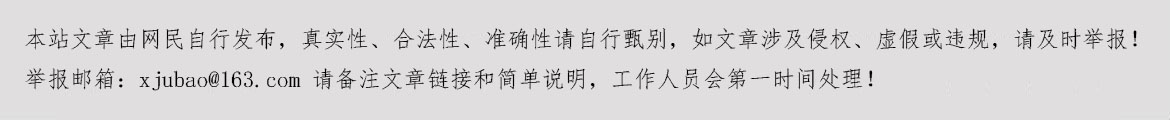想去更远的地方,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变过,他独自去到的最远的地方是广州,带着迪克,一路坐飞机过去,学做咖啡。下飞机的一瞬间,虽然又潮又湿又闷,但他觉得,世界前所未有的开阔。他还跟朋友一起去爬华山,站在华山顶,听朋友描述这里多险峻、多美,那是他最希望自己也能看见的一刻——他很难在脑海里还原这些险峻和美。做眼球摘除手术的前一天,父母带他去了北京动物园,趁着眼睛还能看见,「整个都看了一遍」,他记忆里,这个世界最后留下的画面,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和野鸭。
文|聪聪
编辑|金匝
1
早上8点,调音师杨康出发了。他要从北京南六环出发,赶到离家33公里外的大西边给人调琴。
一进门,他先是找到钢琴的位置,打开钢琴的顶盖和侧板,坐下弹起了一首《菊次郎的夏天》。从旋律里判断这架钢琴的音准,是杨康的工作。每按动一个琴键,与之相连的弦槌就会击打琴弦,发出声音,88个琴键对应着88个弦槌,还有220根弦,每根弦又对应着一个黑色的调音钉。
杨康接触钢琴已经有25年,辨认哪个音对应的琴弦需要调整,拿出调音锤扭动调音钉到合适的程度,这些并不难,难的是按时到达这里,坐在钢琴前——他是一位视障人士,调音时,一直陪在他身边的,是奶茶色的导盲犬迪克。每当他调音时,谱架处的黑色琴面上倒映出他的脸,两侧颧骨往外凸起,会让人想到动画片《心灵奇旅》的男主角乔伊。
杨康不是天生就看不见。11岁那年,由于患上视网膜母细胞瘤,他摘除了两只眼球,眼睛变成了两个黑洞。为了不吓到人,他在眼眶里安了两只义眼。治疗的过程中,眼睑的功能遭到破坏,他不会闭眼,也不会再流泪了。虽然杨康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但顾虑到别人的感受,他还是继续戴着眼镜。
接触到琴不是励志,更多时候是没得选,看不见以后,杨康的母亲没有跟他商量,直接买来一架电子琴,跟他说,你就学琴吧,说这话时,上课的老师已经站在了他跟前。半年后,他学得不错,电子琴换成了钢琴,一直学了6年。2002年,他考上北京联合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对视障群体来说,他们拥有的选择不多,能够读的专业只有两个:音乐和按摩。他不想学按摩,就学了调音,毕业后,做了一名调音师。
大学跟杨康一起学调音的同学,大多数最后都又去做了按摩,因为无法承受出门的不安全感,和站在陌生人前的胆怯。但杨康不行,他闲不住,即使不方便,他也是要出门的,教人弹琴、卖乐器,还去苹果店做销售——直到做了调音师,他不再变了。
志华也是这样一个闲不住的人。他的视力是一点点消失的,从10岁开始,眼前就一直灰蒙蒙的,然后越来越暗,越来越暗,直到十七八岁,一点都看不到了。
后来他学了声乐,大学毕业后,他去艺术团待过,当过朗诵演员、电台主持,还在公益机构做过培训师,教别的视障人士怎么独立出门。看到他本人,你可能会记起来,娄烨的电影《推拿》里,他演按摩店里的一个盲人,是个小角色。
2019年,志华进了滴滴,成为一名企业社会责任经理,和视力正常的人一样每天坐地铁上下班。每天,他都会带上一只叫芒果的导盲犬,用手机、电脑的读屏功能处理工作时,芒果就乖乖地趴在他的工位底下。
志华说,过去他总听到别人评价他「不安分,不守己」,好像因为眼睛看不到,他就应该一直戴着大墨镜,更加安分守己一些,但他知道,那一定不是他要的生活。
杨康和迪克
2
和正常人相比,视障人士如果喜欢折腾,热爱生活,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原本,杨康住在唐山,那是他的故乡。前几年,每次他都提前在手机上联系好客户,坐火车来北京一次,调完音再回唐山。2019年,他结婚了,开始搬到北京的南六环常住。
在偌大的北京,调音这个工作,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抵达目的地。客户分布在全城的各个方位,各个环路,没有手机导航和导盲犬的时候,杨康只能问路,什么时候能赶到,全凭运气。4月20号这天,他接了三单,就分别在北京的西四环、北五环和北六环。
还好有迪克。之前杨康出门靠盲杖,心里总没谱,走路怕前面有东西撞上,或者掉进沟里,迪克填补了这份不安全感,需要央求人的事儿,现在迪克就能帮他解决。对杨康来说,迪克就像孩子一样,每隔一两周,他就会带迪克出去洗一次澡,洗澡用的沐浴露,他会特意自己带,买的都是进口的产品。
为了迪克,杨康等了5年。2012年,他提交了认领导盲犬的申请,当时,全国导盲犬不到30条,培养一条导盲犬的费用极高,大约需要15-20万,仅筛选就有重重标准,上溯三代都要有纯种血统,没有伤人记录。但导盲犬机构不会向使用者收取任何费用,只靠政府补贴和公益捐赠维持正常运转。直到今天,全国的导盲犬数量还不到200条。2017年,杨康接到大连导盲犬机构的电话,让他到大连和迪克共同训练一个月,看他和迪克是否能相互适应,他形容那一刻的感觉,「像飞了一样……我也终于排上队了」。
但也是因为有了迪克,杨康此后出行时遭遇的冲突更激烈了。更多时候,这些冲突和他看不见无关,更接近于外部世界主动制造的一些障碍。
刚把迪克领回唐山,杨康就遇到了新的问题:坐公交车时,司机不让迪克上来,杨康拿出导盲犬使用证、登记证和免疫证,告诉司机这是导盲犬,国家规定的,导盲犬可以出入任何公共场合,包括公交车和地铁。司机说:「管你什么犬,就是狗,就是不让你上。」第二天,他跑到公交公司去投诉,还打了市政府热线,公交公司的领导出来,司机的态度才缓和。
有时候,司机让上,也不代表杨康和迪克可以正常乘坐公交,反对的声音来自乘客,即使司机帮忙说情,对方也能一直骂到下车。
打车会更便捷一些,扬招的话,要看运气,站在路边,一直伸着手,有车停下,他才能上。后来杨康开始使用滴滴,一开始也会遭遇不顺。不止一次,他用滴滴叫到了车,司机来了就拒载,说公司规定,乘客不能携带大型宠物。他解释,这不是大型宠物,是导盲犬,对方依旧不同意。还有一次,一位司机懒得跟他争论,说去打电话问一下公司,让他在原地等着。那是炎热的盛夏,马路热到发烫,几分钟后,旁边有人好心提醒杨康,司机已经走了。
即便是成功抵达客户家,又会有新的问题。杨康记得,2009年,他有次上门给人调琴,公司不放心,找了个同事陪他,那天下着雨,等他赶到客户家里,对方打开门一看,问怎么是两个人来调琴。他解释,自己是盲人调音师。结果对方的态度急转直下:「啊,这个瞎子我不用,我不相信瞎子调琴,你赶紧走吧。」还扬言要投诉,怎么派个瞎子来调琴?「啪」就把门关上了。这样的事发生了不止一次,还有人说出顾虑:盲人调琴,万一把琴调坏了怎么办?
迪克是一只5岁的拉布拉多,站起来能到杨康胸前。他带着迪克到客户家里,对方一看这么大一只狗,立马拒绝让他进门。杨康解释,这是导盲犬,不会伤人。但对方有时候会找一些理由:家里有小孩、对狗毛过敏,或者让把迪克拴在楼道里。杨康一般会拒绝,因为导盲犬在工作的状态下不能离开主人,还有就是,杨康也舍不得。
迪克陪着杨康在客户家调琴
3
杨康是遇到困境更愿意花时间去抗争的那一类人。打车遇到滴滴司机拒载他和迪克,他就打客服电话投诉。司机一溜烟儿跑了的那次,他和妻子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视频去反馈意见,滴滴的安全部门后来直接联系到他本人,跟他致歉。
他很早就意识到,只有抗争,才能给自己争取自由的空间。杨康大专毕业后,继续专升本,但本科只有按摩一个专业,他住在北京的地下室,一边上学,一边到咖啡厅给人弹琴,一晚上二百,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机会,没活的时候,他也接一些按摩的单子。
想去更远的地方,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变过,他独自去到的最远的地方是广州,带着迪克,一路坐飞机过去,学做咖啡。下飞机的一瞬间,虽然又潮又湿又闷,但他觉得,世界前所未有的开阔。他还跟朋友一起去爬华山,站在华山顶,听朋友描述这里多险峻、多美,那是他最希望自己也能看见的一刻——他很难在脑海里还原这些险峻和美。做眼球摘除手术的前一天,父母带他去了北京动物园,趁着眼睛还能看见,「整个都看了一遍」,他记忆里,这个世界最后留下的画面,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和野鸭。
志华的成长也是类似的,普通孩子在小时候,大家的愿望是当科学家、画家、音乐家,但对于视障人士来说,未来的愿望大多数都是「我要当一个好的按摩师」,再牛气一点,就是开一个特别大的盲人按摩店。
志华的父亲也是如此,花钱给他开了一家推拿店,焊了一个特别结实的按摩床,还找人到处贴小广告,但他不想被困在这家推拿店里,试着跟父亲提这件事,说不想20岁就看到70岁,自己永远围着一张按摩床。果不其然,父亲生气了。
志华不甘心,一个人跑到长春考大学,跟着艺术团四处演出。因为跟更多的人接触,他发现周围的人对视障人士的刻板印象太深了。后来,他离开艺术团去了一家公益机构,和更多的视障人士到北京的大学或者社区里给大家讲段子,就是想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有一次,他去北京理工大学,刚进门,学生们怕他看不到跌倒,恨不得三五个人把他抬起来走,他在台上讲段子,下面的人也不敢笑,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学生们才慢慢放开,再去厕所,就变成只有一个学生领着一群视障人士去了。
但即使知道信息差会带来的误解,领养了芒果之后,经常出现的难题还是让志华很愤怒,甚至跟人吵起来。导盲犬上街有「四不原则」:不抚摩、不喂食、不呼唤、不拒绝。这是为了防止导盲犬养成工作中玩的习惯。但路人们看到芒果,还是忍不住想逗,有一次,他听到旁边有个人对芒果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就阻止对方说别逗它,结果对话就变成了,「我没逗它」「那你干嘛」「你管得着吗」。
带芒果上公交车或地铁,志华也要跟人解释半天,打车,还总是遇到拒载的,有时候,出个门要花40分钟才能上车,中途换好几个司机,一个接着一个的拒绝,让志华的情绪也变得急躁。那段时间,他的朋友们都看出了他有些「神经质」,跟他说,感觉他养了一条狗,性格都变了,以前不是这样的。
但志华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和这些人说个明白:「我不难为他,他就得难为我,我难为他之后,才能出来帮咱们解决这个事。」
志华和芒果在使用滴滴叫车
4
滴滴公益的负责人罗真真刚接触到视障群体时,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这群人很容易激动。一开始她觉得,公司已经在制度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可能是个例,但后来接触得越来越多,她才发现大家缺乏对无障碍的理解:滴滴允许导盲犬上车,但也给予了司机拒载大型宠物的权利,视障人士只看到了前者,而很多司机只看到了后者,这中间的矛盾怎么解决?
志华也问过一些司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状况,司机们的反馈是,可以搭载视障群体,但对导盲犬,他们一无所知,有许多担忧:万一咬坏了后座,或者在车里乱跳影响开车,结果谁来承担?
2019年10月,滴滴公益组织了一场无障碍恳谈会,邀请了志华和其他视障、听障群体。在恳谈会上,罗真真才意识到,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细微之处,对这些群体来说是巨大的不便。比如正常来说,滴滴司机到了指定地点,会打着双闪等乘客自己找来上车,但视障群体根本看不到双闪;等到了目的地下车时,滴滴为了安全提醒,会有一个语音播报,「乘客注意前后方来车」,但对视障群体来说,这同样也是没法做到的。
知道了这些人的具体遭遇后,罗真真也明白了他们最初的激动和愤怒。2019年底,滴滴制定无障碍出行项目的具体计划,推出了「无障碍专车」,并持续优化APP信息无障碍功能,盲人群体可以通过语音读屏顺利打到车。原本志华就经常打滴滴的客服电话提意见,后来,滴滴主动联系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到滴滴工作,因为他比任何一个员工都有足够的说服力去提出那些真问题。
最初上线的服务,是针对有导盲犬的视障群体,滴滴联系了导盲犬机构,找到目前正在服役的近200条导盲犬,给这些导盲犬的主人一一实名认证,在他们打车时,滴滴会有语音播报,提醒司机这是一位带有导盲犬的乘客。
导盲犬在滴滴车内
滴滴还想到了定向招募愿意给障碍群体服务的司机,但志华并不认同,他担心,万一只招募到一两千,甚至一两百怎么办?「所有的司机都应该来完成这个工作。」转折发生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为了接送医护人员,滴滴定向招募了医护车队,当时有16万司机加入,这打消了志华的顾虑,在生死关头,还有16万司机愿意加入,那愿意加入无障碍服务的司机肯定更多。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无障碍出行项目上线不到一年,已经有180万司机加入。志华开玩笑,很多司机加入之后,「跑一辈子网约车,可能都拉不到一条导盲犬」。
项目落地后,志华发现,想要实现真正的人性关怀,最难的永远是琐碎的细节。他们在滴滴新版APP中加入了针对障碍群体的特殊的语音播报,「乘客主动上车」,变成了「司机寻找乘客」。「让乘客注意前后方来车」,改为了「让司机注意乘客前后方来车」。
滴滴的无障碍公益项目正在从带有导盲犬的视障群体扩张到所有视障群体,近期,滴滴又与中国盲人协会签订战略框架协议,以进一步推动视障人群的「无障碍出行服务」。下一步,项目服务的对象会扩张到所有的一级盲人,也就是完全看不到的人群。
现在,杨康打车去调琴,很少再碰到拒载的情况。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计划,未来和妻子带着各自的导盲犬自驾去一趟西藏。他明显感觉到,现在出行,比十年前更自由了。在没有智能机的时代,他短信都没办法看,发短信也只能是一串拼音,经常发过去是一串乱码。但现在,还没有见到司机之前,双方就达成了默契,不用再忍受漫长的等待。
杨康和他的妻子